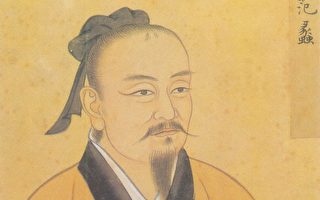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“人才济济、群星争辉”,这些人才往往被“超常”拔擢,就像殷代贤相傅说出身于建筑苦力,商朝贤相伊尹出身于陪嫁的仆役之列,卓然不群。汉朝的大臣,如公孙弘、卜式、兒宽他们天生就像大鹏,却被困在麻雀之群,长年处于卑微之地,然而他们又如何扭转人生、一展鸿图呢?
汉武帝登基时,距离汉朝开国已六十多年,经过文景之治,国内太平安定,财富充盈,但四方外族尚未完全臣服,制度仍有缺漏。汉武帝急于得到修文兴武的良材,求贤若渴,于是他用迎贤之车——蒲轮[1]去迎接贤士枚乘,见到主父偃时更是感叹知音难遇。汉武帝求贤之心的真切,打动了天下有才能有识见的读书人,于是他们抱着一展报负的理想前来献策,奇才异士也纷纷出现。
海边放猪户扭转人生
公孙弘出身齐地菑川的贫穷人家,年轻时当过监狱小吏,因为犯罪而被免职,丢了工作的他生活困顿,只好到海边放猪维生。对他来说,失败的大半生就此盖棺论定吗?且慢!他在七十岁时终于咸鱼翻身,得到封爵拜相,他是怎样做到的呢?
公孙弘四十余岁时,感到人生灰暗,毫无亮点,这不是他想要的。汉代时,今、古文经的研究非常兴盛,于是他开始研读《春秋》经与诸子杂说,立下志愿由儒学这条路走上仕途。岁月悠悠,就这样一埋头二十年又过去了。
武帝初登基,广招天下贤士。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,在地方有名声,被推举为贤良方正。他得到武帝召见赐予博士之衔,派他出使匈奴。但是他的外交辞令并不出采,不合圣意,武帝大怒。公孙弘因而以病为由辞官,归返故里。他对继母孝顺恭谨,继母死后为她守丧三年。
数年后(元光五年,公元前129年),当武帝再度征选文学贤才时,地方又荐举他。他说自己上次已试过不合帝用,请地方更选人才,但是地方还是力荐他,他终于再度受命入京,这一次官至太常博士,负责掌管国家礼仪和文教事务,属于九卿之一。这次的职务,终于和他的本命合盘了,后来更是蒸蒸日上,开创了新局。这位被武帝骂退的人,如何改变了武帝对他的看法呢?
汉武帝求治若渴出考题
汉武帝深切关怀治世之道,冀望达到太平之世。他给来应策的诸儒出考题,让每人上策来答复。他的策问上穷碧落下黄泉,纵贯古今历史,广及各种施政要题,进而追索超越凡间的幽冥之理、生死之变和兴衰之道的深邃因由,最终落在“为政怎样达到理想的上古盛世,如何作到天人合一之道”的焦点上。他关注的这些施政焦点都展现在他对诸儒生的策问中。[2]
公孙弘应试策问写得很详尽周到,他答道:
“臣听说,上古尧舜之治,不靠赏赐官爵而人民能向善,也不靠刑罚人民即自发远离犯罪,根本在于君主正其身,对待百姓讲诚信;到了末世时这一切则完全相反了。厚赏不足以劝善、重刑不足以禁非,正本清源,必要的是君主的信!君主治理国的根本之道有八:用对官吏,则各项职务得以治理;去掉空话、无用的废话,则事情能有效办成;不作无用的建设和器物,则赋敛省;不耽误百姓农事、不妨碍民力,则百姓富有;使有德者进,无德者退,则朝廷尊贵;让有功者上,无功者下,则满朝群臣皆俊彦;罪罚得当,则奸邪能止;赏贤得宜,则臣下劝善。
“对人民来说,身有财产即不争,公平对待则不怨;人伦尚礼则不暴,受到爱护则亲君长,这是想得天下之急务。落实到政治上来说,实施法律的精神能守住义,则人民服从而不离心;君主展现和气有礼的身教,则人民亲切爱人不犯暴行。
“故而,法律用罚,实际是去义的表现;和气待人接物,真正是礼的彰显。礼义正是收拢民心的关键,对人民的赏罚能正用礼义,则人民不犯罪。古代仅仅以衣冠、章服的差异做区别,人民就能守住礼义之道不犯刑罚,就是礼义治国的根本力量。”
在公孙弘的施政对策中,他强调礼义感化教育人民之功,强调治国的基础在于君主己身的诚意正心修身,展现他儒学功夫的精髓。
他进一步献策说:
“臣听说,气相同就会随从,声相近就会相互呼应。同理,君主合德于上天,百姓则随和于下。古代圣地贤君治世时,天地阴阳调和,风调雨顺,甘露普降,五谷丰收,牲畜兴旺,嘉禾并生,朱草萌芽,山林不枯,水泽不干。这就是君主修和气所达到的至高境界。君主高德配天地,光明并日月,感应麟凤、龟龙双双而至,河出图,洛出书。远方外国的君主莫不悦君主之义,奉币来朝,这是和气的极至呀。”
得明主赏识
这次受策问的儒生有上百人,公孙弘的名次本被太常排在很后面,然而武帝对他的对策极赏识,挑选他为第一名。他被召入宫中,容貌甚丽,举止谈吐儒雅有礼,拜为博士,在金马门待诏。
他又献策要选用正直的官吏,恢复古代的风气,矫正当下的弊端——“今世之吏邪,故其民薄,政弊而不行”。他听说“周公旦治天下,期年(一周年)而变,三年而化,五年而定。唯陛下之所志。”
武帝问他:“你觉得自己跟周公的贤能相比如何?”
公孙弘说浅薄如己,不敢相比,但又强调君主有心,效法周公的治国之道,人心对于利害与好恶是可以教化的,就像驯养猛兽令其完全听从于人是可以做到的,拉直曲木甚至不用一日的功夫,他觉得教化民心,一年之期都嫌长。汉武帝看到他的对策,直觉他非是一般的凡夫俗辈!公孙弘提倡春秋大义,尊崇儒术,正符合了汉武帝积极图治的愿望。
公孙弘识见广博而且谈吐诙谐。在朝会时,他不会起廷争,只是陈述分析事端,使君主自作选择。武帝观察他谨慎宽厚,辩论有余,熟习礼仪法律之事,又能以儒术来融通。一年内,武帝就提拔他为左内史。他在内史任内数年,政绩清明,接着升任御史大夫,后来更由御史大夫破例升任丞相,改写了汉朝的制度。
朝廷在东方设置苍海郡,又于北方筑朔方郡。公孙弘数度上疏,认为那荒远之地不切实用,只是耗损中原财力民力,主张罢撤。武帝命朱买臣等人与他辩论,提出十策,公孙弘却无一能答。这让他自知见识不足,乃向皇帝谢罪:“臣乃山东鄙人,不识此地利之便,愿撤西南夷、苍海两郡,专力奉朔方。”得到武帝肯定。
节俭自持 轻财重义
公孙弘常对人说:“人主的毛病,在于不够宽宏;人臣的弊病,在于不知节俭。”他一向以节俭自持。
在元朔年间,公孙弘当了丞相,在当朝引起不小的关注和波动,因为自汉朝建立以来,丞相一职都是封了爵的列侯才能担任,而公孙弘当时并没有爵位。然而公孙弘的德与才深受武帝赏识,武帝特地给他开了门路,亲下诏书:“朕敬仰古代圣贤的做法,愿意打开门路,广纳天下贤士。古人任用贤能,授官看能力,功劳大的得厚禄,德高的获尊爵。……”公孙弘对礼乐教化的大力提倡受到武帝褒奖,为他开了新制,特赐予平津乡六百五十户的封地,封爵“平津侯”。汉朝的丞相加封侯爵,便是从公孙弘开始的。
主爵都尉汲黯在任上素来直言不讳。他对公孙弘入仕晚于自己但官位却升到自己之上心怀不满,在朝上批评公孙弘道:“公孙弘位居三公,禄厚且位尊,却用布被,这是虚伪钓名的作法。”
武帝问公孙弘此事,他坦然承认道:“臣确有其事。九卿之中,与臣最相善的就是汲黯。今日他当庭的诘问,正道中臣之病,就如汲黯之言,如果没有他,陛下怎能知道这件事?臣身为三公,而用布被,与小官吏无异,实在是钓取节俭之名。”可见,公孙弘此番回答避免了在庭上公开和汲黯发生矛盾。
接着他又上奏道:“昔日管仲相齐,用度奢侈几与国君相同;桓公称霸天下也僭越了国君之权。相反地,晏婴事景公,饮食不重肉,妾不穿丝衣,过着如百姓般的日子,也能把齐国治理好。”武帝听后,认为他谦退,益加器重他的贤能。
公孙弘在七十岁时扭转了人生,以儒学治国之道胜出,而在此之前他已然默默耕耘了三十年,这种深耕的功夫,不为寂寞所动的坚持,对后人也是一种鼓舞!
历史评价
公孙弘位居宰相,他建造客馆,开东阁(开东向小门)以延揽贤才,共同参谋施政之议。他受封列侯,然所用的都是粗布衣被,所食仅是糙米饭,一餐中仅有一道肉食。他所得俸禄都用来供养故旧和宾客,积蓄毫无剩余。他在丞相、御史位上有六年,年八十善终于丞相之位。汉平帝元始年间,朝廷修撰功臣列传,天子下诏,褒扬公孙弘道:“自高祖建国以来,辅弼之臣虽多,能身行俭约、轻财重义者,未有如公孙弘的。”
然而,太史公在《史记‧平准书》中对“公孙弘以汉相,布被,食不重味,为天下先”的评价是“无益于俗,稍骛于功利矣”,就是说公孙弘身为汉朝丞相,以节俭自持成为天下人的榜样,然而这种做法并未能有助于改善民风,反而显露出追求功利之心。为什么呢?从现实来看,他轻利散财以招揽贤才,意在追求从政有所作为。
《汉书》指出“其性意忌,外宽内深”,同朝的主父偃在身败后被诛杀、董仲舒遭迁徙胶西(后来因病免)都和他的“进一言”有关。如果他了解说话伤人的可怕,能宽和、慈悲于人,不给自己造口业、造恶业,那么他的成就光谱自然大不相同,生命也会升华到不同境界了。
注释
[1] 古时迎聘贤士,以蒲草包裹车轮,使车子行走时减少颠簸,坐起来安稳舒适。
[2] 汉武帝的策问:“朕有所听闻,上古太平盛世的时候,虽然只是靠衣冠服饰来区分尊卑贵贱,百姓却都守礼不犯。天地阴阳调和,五谷丰收,牲畜兴旺,甘露降临,风调雨顺,嘉禾并生,朱草萌芽,山林不枯,水泽不干。麒麟凤凰出现于郊野,神龟蛟龙现踪池沼,黄河出图、洛水出书。人能正常寿终而终没有夭折早亡的,因此父不丧子,兄不哭弟。北方开渠引水,南方安抚远地,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,人迹皆可遍及,无论飞禽走兽,都各得其所、安然自在。
“朕对这样的太平景象非常赞叹。如今要走什么样的道路,才能再现这样的盛世呢?大夫您博学多闻,修习古圣之道,议论精辟,名声远播于世。今日特向您请教:天地与人之间的道理,根本何在?吉凶的预期,怎样才能得以应验?圣帝大禹商汤时代也有水旱之灾,咎由何在?对于人民施行仁、义、礼、智的教化,该如何作才是合宜?王朝的道统与德业的延续,生死的变化,天命的符应,兴衰之因何在?各位大夫熟习天文、地理、人事这些大事的法度与准则,务求无所隐瞒撰写成文,朕将亲自阅读。”@*#
——资料来源:《汉书‧公孙弘卜式兒宽传》《史记》
责任编辑:王愉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