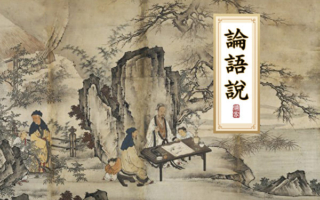子贡问曰:“赐也何如?”子曰:“女,器也。”曰:“何器也?”曰:“瑚琏也。”(《论语‧公冶长‧四》)
【注释】
瑚琏:音hú liǎn,古代祭祀时用来盛黍稷的器物,宗庙之器贵者也。另,屈万里教授说瑚琏实即胡辇,而胡辇即任重致远的大车。
【讨论】
子贡被称为孔子最亲密的弟子。《论语》中记述孔子与弟子答问,以子贡为最多,次数远超出镜率高的颜回、子路。子贡自身学问也甚了得,入列 “孔门十哲”。而在世人眼里,子贡才能卓绝。不仅“言语”水平高超,而且为儒商鼻祖、富可敌国,还曾任鲁国、卫国的丞相,至于纵横术更在苏秦、张仪之先。
本章之前,孔子已点评了公冶长、南容、子贱,子贡平日好比方人物,见不及于己,有点按捺不住,跑去问孔子“我怎样呀?”孔子答曰“女器也”。这似乎在敲打子贡,因为孔子说过“君子不器”。子贡不甘心,接着问“我是何种器呀?”孔子说:你像是放在宗庙中盛黍稷的瑚琏。瑚琏乃宗庙之器贵重而华美者也。意子贡能堪当大任,以荐鬼神、羞王公矣(可上荐鬼神,下供王公贵卿重用)。本章后演化出一个成语——“瑚琏之器”。
孔子对子贡的才能多有肯定。例如,孔子曾对季康子说“赐也达,于从政乎何有!”(雍也篇)本章说子贡是“瑚琏”,则有褒有贬。褒者,才能之高雅贵厚也;贬者,未至于不器也,距离君子的至高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宋人张栻解读本章:子贡之问,盖欲因师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。而夫子告之抑扬高下,所以长善而救其失者,备矣。谓之器,则固适于用,然未若不器之周也;谓之瑚琏,则以其美质可以荐之宗庙也。然瑚琏虽贵,终未免于可器耳。赐也味圣人之言,意即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,则亦何有穷极哉!
要指出的,本章亦庄亦谐,读者亦庄亦谐读之,更见其妙。
最后讲个故事,或许能有助于读者理解孔子为什么把子贡比做瑚琏。根据《史记‧孔子世家》所述,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遭遇一次危机: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,孔子准备前往拜见回礼,却被陈、蔡两国大夫发兵围困在陈蔡之间,断粮七日。随从的弟子疲惫不堪,饿得站不起来;孔子仍讲习诵读,演奏歌唱,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。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恨之心,就分别召见子路、子贡、颜回,问到:“《诗》中说:‘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,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。’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?我们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?”
其中,子贡的回答是:“老师的学说极其弘大,所以天下没有国家能容得下您。老师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呢?”孔子说:“赐,优秀的农夫善于播种耕耘却不能保证获得好收成,优秀的工匠擅长工艺技巧却不能迎合所有人的要求。君子能够修明自己的学说,用法度来规范国家,用道统来治理臣民,但不能保证被世道所容,如今你不修明你奉行的学说却去追求被世人收容。赐,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!”
再看看颜回的回答:“老师的学说极其弘大,所以天下没有国家能够容纳。即使如此,老师推广而实行它,不被容纳怕什么?正是不被容纳,然后才现出君子本色!老师的学说不修明,这是我们的耻辱。老师的学说已经努力修明而不被采用,这是当权者的耻辱。不被容纳怕什么?不被容纳然后才现出君子本色!”
两相比较,子贡与颜回的差距不是一点点,“君子不器”对子贡尚可望而不可及。
但请注意,孔子最后如何走出这场危机的呢?“于是使子贡至楚。楚昭王兴师迎孔子,然后得免。”这里子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。因此,比子贡为“瑚琏”,亦恰如其分。而孔子之因材施教、知人善任,由此可见一斑。
主要参考资料
《论语注疏》(十三经注疏标点本,李学勤主编,北京大学出版社)
《四书直解》(张居正,九州出版社)
《论语正义》(清 刘宝楠著)
《论语新解》(钱穆著,三联书店)
《论语译注》(杨伯峻著,中华书局)
《论语今注今译》(毛子水注译,中国友谊出版公司)
《论语三百讲》(傅佩荣著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)
《论语译注》(金良年撰,上海古籍出版社)
《论语本解(修订版)》(孙钦善著,三联书店
子贡:孔子最亲密的弟子 https://www.sohu.com/a/390969353_281788
看更多【《论语》说】系列文章。
责任编辑:林芳宇@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