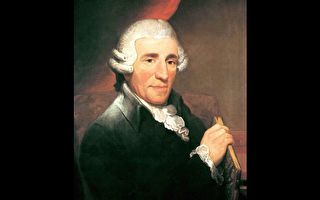【大纪元2025年10月19日讯】那是九月中旬一个令人屏息的夜晚,纽约中城的圣母玛利亚教堂(Church of St. Mary the Virgin)石造的高耸拱顶,传来充满震撼的回响,使音符仿佛漂浮于空气中,这是首位获得葛莱美奖的管风琴家Paul Jacobs的独奏音乐会。当第一个和弦响起,观众瞬间被带回1840年——孟德尔颂(Felix Mendelssohn)演出巴赫管风琴音乐的年代。
纽约重现1840年巴赫音乐会
隐身在教堂二楼的管风琴廊里演奏的Paul Jacobs,双手飞舞于层层键盘,双脚在踏板上灵巧移动,像是同时指挥一支看不见的管弦乐团。从轻柔的长笛声,到锐利直透的簧管音,到空灵的超现实音色,都在他的掌控下徐徐展开。当《C小调帕萨卡利亚与赋格》(Fuga a 3 Soggetti)结尾的强音响彻教堂,震撼的和弦久久回荡。观众屏住呼吸,直到最后一个音符消散,才如释重负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
这场音乐会,现场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,让笔者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理解,为什么管风琴会被称为“乐器之王”。这位茱莉亚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管风琴系主任——Paul Jacobs演奏的背后,又有哪些令人感动的故事?
用心体会传统音乐的震撼
“传统音乐具有永恒的魅力,是代代相传的宝藏。这些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音乐,应该要被传给未来世代。这些是人类音乐成就的高峰,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去体验。”在访谈中,Jacobs这样解释他对巴赫、孟德尔颂等传统音乐的执著。他相信,这些流传数百年的作品是人类文明最闪耀的成就,值得一代又一代传承。
然而,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改变。当下的听众习惯于社交媒体上的短片,追求快速的感官刺激,却少了静心沉浸于长篇作品的耐性。“我担心我们正在失去反思的能力。”他语气平静,却带着警醒。对Jacobs而言,音乐不只是娱乐,而是一种培养内在生命的方式。
在圣母玛利亚教堂的音乐会上,Paul Jacobs演奏了巴赫最知名的作品之一——《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》。这首曲子戏剧性极强,开头像电影般震撼,随后的旋律则层层推进,让人感到心灵被不断牵引。虽然它已经流传数百年,但对Jacobs来说,每次演奏依然新鲜、充满力量,尤其是后半段的赋格,深深打动着他。

当晚的曲目中,无论是开场庄严的《圣安妮》三重赋格,宏伟的《帕萨卡利亚》,还是火热奔放的《A小调前奏与赋格》,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。Jacobs解释,绘画或建筑虽然伟大,但它们一旦完成便静止不变;而音乐却不同,它必须透过当代演奏者的双手与心灵重新唤醒,才能真正活过来。录音固然珍贵,但仍无法取代现场音乐在空间中回荡时带来的震撼与灵魂触动。
这场演出,他特意要求观众不要在曲目之间鼓掌。“因为这次的曲目性质,以及我演奏时是被隐藏的,我希望大家单纯专心去聆听音乐,等到最后一个和弦结束,回响消散之后,再去回应。”那一个小时不间断的演奏,像是一场洗礼,观众全然沉浸于音符之海,而演奏者则只是媒介,让巴赫与孟德尔颂的精神透过乐器再次发声。
巴赫的《约翰受难曲》是Jacobs心中最珍爱、最愿亲身沉浸其中的作品之一。他曾经在采访中说:“我们常常忘记,‘Passion’不仅仅意味着强烈情感,更确切的意思是‘受难’或‘忍受’。巴赫的音乐正是表达了这一点——基督为了人类所承受的巨大痛苦。巴赫将基督的痛苦转化为美的音乐形式,而这音乐也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希望。”
少年邂逅“乐器之王”
Paul Jacobs的音乐之路,起点并不在纽约大都会,而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镇。家中虽然没有音乐世家背景,但母亲早早发现他的天赋。四岁时,他就对姐姐的钢琴课充满兴趣,坐在角落里听得目不转睛。很快,他也开始了钢琴学习。
十一岁那年,Jacobs第一次在教堂中接触到管风琴。那庞大的乐器,需要双手和双脚同时配合,他必须长到足够高,才能踩到踏板。“管风琴是所有乐器里最‘身体化’的。”他回忆道,“因为必须用脚来演奏音乐,这是其它乐器没有的。”
虽然身处小镇,他却幸运遇到良师益友。当地学院的音乐系主任与教堂的管风琴师,给予他不只是技巧,更传递了对音乐的热爱。这份早年的启蒙,奠定了他一生的道路。十五岁时,他已被任命为一所拥有三千五百名教友的大教堂首席管风琴师,“少年天才”的名声逐渐传开。
挑战十八小时的演奏极限
Jacobs的名字真正被写进音乐史,则是在他二十三岁时。那一年,他于巴赫逝世250周年之际,挑战十八小时的“巴赫管风琴全集马拉松演出”。
演出从清晨六点开始,以《圣安妮》前奏曲揭幕,直到次日凌晨零点十八分结束。十八小时,数以百计的乐章,无数次的换气、转换音栓,他几乎将全部生命燃烧于琴键与踏板之上。
“筋疲力尽,但无比快乐。”他说。这场马拉松式的壮举,让观众首次在短时间内完整接触巴赫的音乐宇宙,也奠定了Jacobs作为当代巴赫诠释者的地位。
之后,他成为唯一一位获得葛莱美奖的管风琴家。2011年,他凭借梅湘《圣体之书》的录音获得殊荣。对他来说,这不是个人荣耀,而是管风琴这件乐器再度被看见的时刻。

管风琴——乐器之王的奥秘
Jacobs喜欢把管风琴比作“一个看不见的管弦乐团”。确实,它是人类设计最复杂的乐器之一,拥有数千根音管,能同时展现旋律、和声、对位,音色变化如同整个交响乐团。
“和钢琴相比,管风琴没有统一标准。每一台都是独一无二的。”他解释。这意味着,每次演出前,他必须花上一至两天熟悉乐器,为曲目设定上百种音色组合,就像厨师在设计一份新食谱。“这非常耗时,但也让每一次演出都成为全新的体验。”
在一些演奏场所,例如在圣母玛利亚教堂演出时,观众甚至看不到演奏者。声音从教堂高处传来,有时还带着延迟。“这也是管风琴家的挑战,”Jacobs笑着说,“就像在指挥一个庞大的管弦乐团。”

为什么要坚持传统音乐
在流行文化、速食文化充斥网络的时代,为什么还要坚持演奏几百年前的作品?Jacobs的回答坚定而温柔:“因为这些音乐能够触及人类的精神深处。它们不仅回答问题,还揭开了生命的奥秘。”

他坦言,古典音乐产业往往聚焦于小提琴、钢琴,而忽视了管风琴。但他从不怀疑这件乐器的价值。多年来,他不仅与世界各大交响乐团合作,也在教学上培养新一代管风琴家。自2003年起,他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任教,翌年即成为该校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。二十多年来,他见证了学生们走向世界,在教堂、音乐厅、学院继续传递这份古老的艺术。
对Jacobs而言,演奏并非重现,而是一种“对话”。当他弹奏巴赫的赋格或孟德尔颂的前奏时,他感受到的是跨越时空的交流。“这是一种与更智慧的灵魂相遇的方式,”他说,“仿佛很久以前的作曲家正在对我们说话,而这些话语至今依然切身相关。”
他引用舒曼的格言:“要与比你更有智慧的人在一起。”对Jacobs来说,管风琴就是通往这样的对话的桥梁。与此同时,Jacobs也是新管风琴作品的推动者,他与许多当代作曲家合作并首演过他们的音乐。音乐不是静止的画作或雕塑,而是必须透过当代演奏者赋予生命的艺术。每一次演出,都是一次灵魂间的再会。
“音乐是我的全部”
如今四十八岁的Jacobs,回顾自己从小镇到国际舞台的旅程,心中满是感激。“这几乎是一个奇迹。”他说。音乐把他带离卑微的出身,让他能在纽约顶级音乐学校教学,与世界最优秀的乐团合作,并周游五大洲,将所爱的音乐分享给无数人。
他坦言自己还未婚,因为音乐占据了他全部人生。“音乐是我的初恋,也是我生命的一切。”这份全然的奉献,或许也是他能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管风琴家之一的原因。
管风琴的声音不仅是乐音,更像是一种来自过去的呼唤。透过Paul Jacobs的演奏,我们与巴赫、孟德尔颂建立了连结,也与自己的灵魂展开对话。
在这个快速、喧嚣的时代,或许正需要这样一种声音,提醒我们停下来,用心去聆听——那种超越时间的美与意义。◇#
责任编辑:李维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