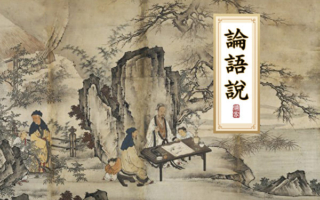东坡闲话 唐明皇因这首诗歌落泪 果真一诗成谶?

东坡作有《渔樵闲话录》,透过一渔一樵(东坡替身)的闲聊,谈世道话见闻,开人眼界。有来客建议渔樵两人聊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的生活小道理,或是对着清风明月,吟诗作对,不要动不动就扯到朝廷政事和历史故事,越俎代庖。那么,渔樵闲话是世间小哲理或是人生大话?或者什么也不是?就交给读者自己体会了。
这一天渔夫和樵夫,继续回忆当年唐明皇(玄宗)的往事(接上回:东坡闲话 打开话匣子:和尚万回的预言):
天宝末期,明皇盛世已经超过四十年,他心中倦怠不想管天下大事,心里盘算着:国家大业交给大臣去料理,朕就在后宫优哉游哉!不巧,他挑中了李林甫这号人物,结果把大唐朝政直送进了大黑洞,一时奸谋诡论四起,忠言议论消声。皇帝本人呢?日夜行乐,忙得不亦乐乎。
有一晚,明皇心血来潮,登上勤政楼(一说花萼楼)赏月,叫善歌者登楼唱水调歌。歌曲转呀转,忽然有词句深深扣动他的心门:“……富贵荣华能几时?山川满目泪沾衣。不见秪(只)今汾水上,惟有年年秋雁飞。”
明皇那时春秋岁数已高,心思容易触景生情,一听此曲就凄凄然,一曲未完,他起身问道:“这是谁作的?”
侍者回禀道:是李峤之作(*李峤,公元645—714年,20岁登进士,曾任宰相)。
明皇说:“李峤真才子也!”说着感慨不已。堂堂太平天子,竟被一首诗感动得七上八下,冥冥中似有伏笔。
到了次年(天宝十四载,公元755年)年底,范阳起乱兵,安禄山进逼皇都。明皇和后宫乘车驾西逃蜀地,路过剑门关,登白卫岭,他放眼环顾山川壮丽、风光无限,却久久闷闷不乐。忽然想起去年在勤政楼赏月听歌时感动他的诗句,就叫人再唱。听着“富贵荣华能几时?山川满目泪沾衣……”感慨不已,依然又是那句话:李峤真才子也!此时,明皇不觉泪沾衣襟,扶着高力士下了白卫岭。

樵夫说了自己的看法:
天下的山川草木这些物质本身不会跑来撩拨人心,对于山川草木的触动全是人心自发自感的作用。天下事也是这样,事情本身并不左右人的心情,可是人的心情却自动门户洞开,让事情来左右着、牵绊着。
李峤作这首《汾阴行》歌行本不是为了明皇而做,当时33岁的他借昔日汉武盛世作了今昔之比以讽刺时事,哪里想到会惹得当时还未出世的唐明皇数十年后老泪纵横?从《汾阴行》作成算起的话,使得明皇老泪纵横那是78年后的事情了,这不是诗有神通之力,而是明皇自己陷于情中不能自拔。
庄子他老人家反问说:“是山林啊、野泽啊,使我欣欣然快乐无比的吗?”(《庄子‧知北游》:“山林与?皋壤与?使我欣欣然而乐与?”)其实山林野泽上的草木自身只管自自然然地滋长茂盛,并不寄情于自己的茂盛能使人快乐!是人自己看着山林野泽的茂盛心生欢喜、感到快乐。所以说,这就是一种“无故之乐”;同理,世上也有“无故之忧”。正因如此,世上之人可能乐未完,哀便来,笑声未绝,泪又随之。(《庄子‧知北游》:“乐未毕也,哀又继之。”)这话真不虚呀!
后人语:人间道
世上有“无故之乐”,那世上又怎来“无故之忧”?东坡以唐明皇听闻李峤诗歌“富贵荣华能几时?山川满目泪沾衣……”的反应作了解答,也真是弹不虚发。是凡世间事、人间情,都是人“心”在作主呀!世间有人想修行,一个重大的原因,就是在历经生老病死、生离死别和名利情的种种无常之苦后,想要做自己的主人。人世纷纷扰扰,人对于情绪“哀乐之来,吾不能御,其去弗能止”,不管是哀是乐,它们要来就来,要去就去,自己无从抵抗,不能主宰,这样的“人”,终究只能当世中事物的旅舍罢了!@
资料来源:《渔樵闲话录》《庄子.知北游》
责任编辑:李梅#